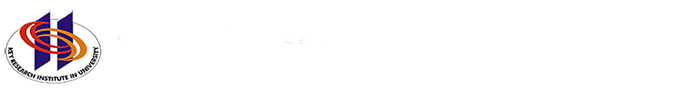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齐格蒙特·鲍曼与文化现代性”学术工作坊
2025年11月6日,“齐格蒙特·鲍曼与文化现代性”学术工作坊在中山大学锡昌堂504会议室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拉筹伯大学荣休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Peter Beilharz教授和Thesis Eleven(《第十一条提纲》)Sian Supski研究员共同组织,特邀来自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以及《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的学者和博士生参会。工作坊分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周晓莹教授主持。
工作坊开始前,张笑夷教授向参会师生表示诚挚欢迎,并在致辞中介绍了举办此次工作坊的初衷和宗旨。她提出,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言,即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无知,满足于对现代性的表面观察,但要想从心中抹去对于我们生活的精神文化根基的追问恐怕是不大可能的。生身为人,我们自然文化地面向生活、面向未来。尤其是人类经历了20世纪深重的历史灾难,正在经历数智技术和智能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对文明样态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只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强烈。作为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现代性文化的拷问者,齐格蒙特·鲍曼自然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世界和当代文化绕不开的思想资源和对话者。今年恰逢鲍曼诞辰100周年,我们举办“齐格蒙特·鲍曼与文化现代性”学术工作坊以示纪念,希望通过组织这样一个跨学科交流平台,深化对鲍曼思想精神和文化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探索人类新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文化建设的可能路径。
工作坊上半场由Thesis Eleven(《第十一条提纲》)编辑Sian Supski研究员、张笑夷教授和周晓莹教授发言。
Sian Supski 以 On the Treachery of Words——The Style of Zygmunt Bauman's This is Not a Diary为题的报告中,选取并分析了鲍曼在2010年9月—2011年3月以讨论条目的方式写作的非日记体的日记。她认为,在这本著作中,鲍曼使用“on”这一叙事工具,写就的文本体例并非严格的学术论文或私密的个人日记,而是一种碎片化、主题化的随笔。与此同时,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文本的线性逻辑,使得鲍曼自由地在个人观察、理论反思和社会批判之间跳跃,形成一种“流动的”写作风格。另外,“on”成为一种邀请姿态,引导读者进入他的思维过程。由此,鲍曼建立自己与读者之间富有感情、极具力量的关系。她强调,根据鲍曼此书的编辑John Thompson所言,在这一著作中既可以看到鲍曼隐私的一面,可以观察到他刻意隐藏的绝望之感,也可以看到鲍曼乐意分享的一面,他乐于把读者带进他的世界之中去消解他的孤独感。通过对鲍曼非私人日记的阐释,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鲍曼晚年复杂且具有想象力的写作风格。
张笑夷教授的发言以“如何想象一个没有伦理立法的道德世界:齐格蒙特·鲍曼的‘元文化’立场”为题。她从如何关注到齐格蒙特·鲍曼谈起,提出了鲍曼对于理解现代世界的重要性。鲍曼不仅对现代性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做出了深刻的描绘,从伦理和道德方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现代世界的文化焦虑做出了理性的分析,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和道德责任。张笑夷教授认为,鲍曼对流动现代性时代的伦理学的建构实际上是想象了一个没有伦理立法的道德世界。鲍曼强调不逃避和不抛弃自己的道德良知以及对道德责任的责任,承担起偶然性的命运,创造属于自己因而也是属于人类的意义世界。这乃是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化精神的自觉。这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可以从鲍曼的元文化立场得到很好地理解。张笑夷教授从鲍曼的后现代视角、关于人类文化事实的考察以及作为实践的文化观念等方面具体阐释了鲍曼元文化立场的具体内涵。
周晓莹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伦理原则的反思——基于儒家伦理视角”。她试图比较儒家伦理思想与鲍曼伦理思想的异同,对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展开讨论。周晓莹教授认为,鲍曼将文化视为人类社会的现实特征,认为它是以理性真理为基础、取代启示的秩序构建方式;区分文化与自然,反思现代文化中自我反思的立场,并指出文化本身具有模糊性,其中内含人的创造性与规范规则间的张力,进而提出“道德时代”的到来,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重要性。从儒家视角看,伦理原则的形成与理性发展相关。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宗教祭祀到人文理性的转向,如商周时期祭祀情感由畏惧转为敬仰,礼乐文化逐渐规范人间秩序。儒家认为人性善恶并存,强调后天教化与理性规范对道德塑造的必要性,与鲍曼认为伦理学常忽视真实道德领域的观点形成对比。儒家理性植根于道德实践与人文秩序(如“孝”从祭祀演化为人伦规范),不同于基于利益或社会结构的现代理性。周晓莹教授认为,尽管鲍曼试图避免道德相对主义,但其后现代伦理学仍面临相对主义风险。
工作坊下半场由周晓莹教授主持,分别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王立秋老师、《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李天朗博士、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陈浩东、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孟繁伯发言。
陈浩东发言题目为“实践的语法:齐格蒙特·鲍曼早期思想中的文化符号学”。他聚焦于鲍曼1968年未发表的手稿《文化理论纲要》,揭示了其早期学术中常被忽略的符号学向度。面对当时文化人类学所面临的解释力危机,鲍曼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鲍曼的文化符号学本质上是实践导向的:文化并非外在的抽象体系,而是一套深植于日常生活的“语法”。这套语法通过符号的创造性运用,既维系社会秩序,又为意义的重构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内在空间。换言之,文化作为“实践的语法”,既规范行为,又因其符号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允许行动者在实践中进行再阐释与创新。这一早期思考,不仅展现了鲍曼思想的符号学渊源,也为其后来关于现代性、伦理与液态社会的研究,埋下了重视实践、过程与创造性的理论伏笔。
孟繁伯的发言题目为“‘自然正当’政治设计是‘怀旧的乌托邦’吗?——鲍曼与施特劳斯的对话”。他认为,基于现代性批判的乌托邦构想可分为“向前看”与“向回看”两类,分别以鲍曼和施特劳斯的论述为典型;二者问题意识相似但解决方案不同,其原因在于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态度存在差异。孟繁伯认为二者与马克思的乌托邦构想构成以乌托邦为主题的正反合辩证关系:施特劳斯的方案实质是退回古典的怀旧乌托邦,构成辩证法第一阶段;鲍曼在其中期著作中深刻批判进步的乌托邦,并试图以“不确定性道德”超越简单反乌托邦,构成辩证法第二阶段。但他始终困于对“否定乌托邦”的再否定,未能找到“向前看”的实践路径。而马克思的方法可以构成第三阶段,揭示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关系根源,从而为超越现代性问题提供可能。
李天朗博士以“现代性、流亡与道德:青年鲍曼的精神史考察”为题发言。他认为,相较于米沃什、柯拉科夫斯基等波兰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自觉,鲍曼的犹太出身与共产主义信仰交织出独特的身份困境。其思想轨迹呈现三重断裂,最终在1968年“三月事件”中被污名化为“境外势力”,完成地理与精神双重流亡。这种“局外人”命运使其超越意识形态与民族叙事,发展出以“为他者负责”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李天朗博士指出,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实则是其创伤记忆的转译,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他主张通过协商对话构建动态激进民主,以道德能动性对抗流动现代性的异化。这种从政治实践到伦理关怀的转向,既折射出中东欧历史剧变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也为理解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理论转型提供了独特样本。
王立秋老师最后发言,他在鲍曼“液态现代性”理论基础上反思了不同学科领域中的文化概念。他提出,文化并非静态“固体”(如标签、固化产物),而是“液态”的意义生成过程。文化在人的实践、思考中动态建构,是“活的传递”而非僵化符号。例如,东方学对“东方”的刻板想象、传统文明研究对“高级文化”的固守,本质是“固体思维”的产物,而文化的真正生命力,在于突破边界、持续互动的“流动性”。在液态现代性中,规则模糊、边界消融,知识分子应以“活的思考”替代表征式解读,通过身体力行回应文化的“他者性”,拒绝将文化简化为符号,而在互动中捕捉其内涵。王立秋提出,可以借鉴人类学“在地性”观察,结合跨学科的相关理论,聚焦文化的动态运作机制与跨文化互动。从文明比较到过程互动的转向,既回应了现代性对传统的解构,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视角。
发言之后,参会嘉宾与Peter Beilharz教授一起,就上述报告内容和相关话题展开了交流与对话。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中,鲍曼的文化理论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讨论和理解。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