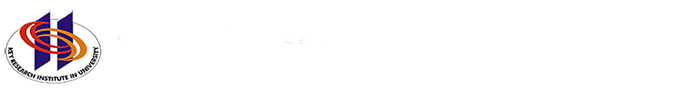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6讲
2026年1月8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六讲“文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之前,吴重庆教授对罗岗教授作了简要介绍,称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当代理论与思想史等领域深耕多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已超越了中文学科,广泛影响了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各个方面。吴重庆教授表示,相信通过罗岗教授的讲述,现场听众定能清晰地把握当下中国文学与文艺的历史源流与发展动向。
一、历史形态中的“文艺”概念
讲座伊始,罗岗教授便阐明了其“文艺”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对“文艺”概念的考察不能延续一般意义上的“关键词”梳理法,因为这种研究思路难免以西方的相关概念作为模板,忽略了对中国时代特色的发掘。如果以西方对“文学”概念的理解,规范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就难免淹没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和丰富潜能。如果要阐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就应该考察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流传入中国之后,遭遇了何种问题和危机,以及为了应对这些危机采取了何种解决方案。
罗岗教授认为,“文艺”概念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为克服西方现代文学传入到中国之后面临的问题而发展出的文学形态。因此,对“文艺”概念的研究需要呈现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罗岗教授将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历史形态中的“文艺”概念研究。
“文学”与“文艺”两个概念的分化,于1947年7月6日初见萌芽。当时,北京大学西语系袁可嘉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一文。袁可嘉认为,“人民文学”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阶段,两者相辅相成。但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政治相结合,“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作为两种具有内在差异的“文学想象”,背后蕴含着的是基于对“中国国情”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两套“政治规划”。“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人民文艺”对应的则是政治上的“人民国家”、文化上的“印刷文化”与“口传文化”杂糅的复合形态、文学上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从这点上看,“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不可能相互包含,圆融一体,两者的鲜明分野预示着人民文艺实践的展开。
1949年,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系统阐述了“文艺”的地位与意义。文章讲到:“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一个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自此,“文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罗岗教授表示,文艺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文学一定程度上是精英化、专业化的,而文艺则更加大众化。从文学到文艺的这一转变依赖于新的媒介手段,新兴媒介为文艺的广泛传播和迅速下沉,提供了历史条件与物质前提。
二、“文学”的“文艺转向”
“文学”的“文艺转向”伴随了三次重要的媒介质变:第一次变革发生于晚清至“五四”时期,其核心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文学的商品化。它催生了现代报刊、出版物等新型媒介载体,重构了文学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模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都市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为主体的“阅读大众”得以形成。第二次变革发生在抗战时期,文艺实践突破了此前以城市为中心的印刷文化逻辑,为应对战争动员的迫切需求而转向农村腹地。它构建了一套跨越识字率壁垒的基层传播体系,综合运用各种媒介形式,将过去被现代文学悬置的农民转化为文艺动员与生产的核心主体。第三次变革浪潮则是1990年代以来,由数字媒介崛起与影像文化霸权所驱动的转型,以互联网、移动设备为载体的媒介生态。这对两个传统构成了双重挑战:其一,是“五四”以来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其二,则是自延安时期以来将组织化和教化功能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
从文学到文艺这一转变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左翼文艺的兴起。罗岗教授引用1931年瞿秋白在《申报》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进行佐证。左翼文艺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本的左翼文学无法承担其所预设的大众化任务,因为左翼文学的受众是具有购买能力、闲暇时间以及读写能力的“阅读大众”,这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无产阶级来说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因此,在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中,“大众”就需转变为具有革命意味和阶级色彩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则专指能够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具有革命引领作用的“大众文艺”。
新的“大众文艺”呼唤新的表达手段,瞿秋白的“大众文艺”思想为文艺形式的改造打开了空间。传统的文艺体裁虽然易于普及传播,但其内容有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众化”的初衷。后来,连环画、左翼电影和现代木刻渐渐成为“大众文艺”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推动了“大众文艺”的进一步发展。
三、“人民文艺”的媒介转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扎根于农村社会。在以口传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化”真正找到它的历史实体。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文学”面对的是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这是一种与以“阅读大众”为主体的都市印刷文化迥异的文化状况,在这种条件下兴起了新的文学形式,也即“解放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限制,发展出“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编历史剧”和木刻、版画、黑板报、新年画等“视听文化”形式。“人民文艺”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史概念,一方面在生产条件上打破了城市印刷文化的限制,拓展到更广泛的传播领域;另一方面赋予了“文艺”新的意涵,“文艺”形成了特定的指向,重新定义了文化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文艺形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从而与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文学”传统之间发生断裂,因此被另称为“人民的文艺”。
“人民文艺”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基层建设实践,其中,在基层展开的以群众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宣传媒介和组织形式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传播有五种类型:一是在农村建立报纸、画报、屋顶广播、幻灯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体;二是以戏剧流动演出队为基础组成的宣传队;三是口号、标语和黑板报等灵活机动的基层传播方式;四是组织群众联欢、英模大会和歌咏比赛等群众文艺活动;五是读报小组、群众大会和扫盲等政治思想教育活动。这些多样化、群众性的基层传播方式,具有“网络化”的特征。“网络化”一般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社会,在根据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依靠群众组织、基层传播形成的网状社会形态,这十分类似于互联网的网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通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基层社会形成了既高度组织化、又具有高度弹性的组织模式,为“人民文艺”的多样性灵活性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罗岗教授认为,“人民文艺”的传播意味着从“消费者的艺术”到“生产者的艺术”的转变。真正具有“人民性”和“大众性”的文艺,也必将是“生产者的艺术”。这种文艺能够打破旧有文化权力结构的垄断,将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归还到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政治生活与伦理世界中去。今天来看,“人民文艺”与当下文化语境的关系看似遥远但绝非断裂。相反,人民文艺的机制与经验展现出一种延绵的生产性,不断为今天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氛围带来必要的警醒和启示,也为新涌现出来的各种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提供资源和动力。
四、“新大众文艺”的诞生
罗岗教授提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大众文化是20 世纪媒介技术、电子记录和传播技术与文化生产和流通资本化等多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在中国,这一进程首先是依靠先锋政党的社会下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精英知识分子的主动传播来完成的。这种历史源流造成了当代中国大众文艺的双重性特质:中国大众文艺既是与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密切相关的“人民大众文艺”,又是和文化工业、文化市场紧密相连的“消费大众文化/文艺”。
罗岗教授指出,以影视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影视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一个对社会表达来说断裂大于融合的二元体系。在市场化的一端,资本往往对文化生产缺乏实践经验和审美辨别能力,仅仅依据市场成绩的好坏作为引进和学习的标准。同时,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一端却没有因此而主动进入这一空白市场,而是进一步退守传统平台,继续进行缺少市场活力、缺少创新和传播力的“主旋律”内容生产。罗岗教授强调,这种文化表征的二元体制不仅仅代表了所谓市场和受众的必然区隔,更重要的是两者所表征的生活世界、社会生活原理和情感结构也越来越泾渭分明。在生产者、生产方式和传播平台的进一步分化下,这种二元体系对于中国文艺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国民共同文化的生产,已经产生了类似于精神内战的负面效果。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二元结构也催生了“新大众文艺”的诞生。“新大众文艺”的创造性变革在于创作主体的变化,普通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中,文艺创作不再局限于专业作家,普通人也能成为作者、艺术家。这依旧得益于新媒介的运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新媒体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创作和传播的门槛。
讲座最后,罗岗教授强调:“一个社会文化生产的实质,是国民共同体在主体性与共同意识层面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民众通过集体经验的媒介化表达与传播,对共同价值的确认与重构以及对不同意见与经验的沟通和协商。”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新大众文艺”,就是进行社会文化的重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富有感召力和时代感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化经验”。这意味着:文艺发展一方面要建立文化主体性,在全球化、市场化的语境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大众文艺;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人民性,确保“新大众文艺”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消费,还能承载公共价值、历史叙事、集体情感等更高层次的功能。
五、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吴重庆教授作出评议,他认为,正如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论述的:如果说革命事业是一部机器的话,那么文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质言之,革命事业中最重要的是将基层群众、基层社会动员和组织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则发挥着看似微小、实则关键的凝结力量。文艺不仅反映着现实中革命事业的发展,更驱动着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及基层群众的组织。
有同学提问:在大众文艺的视野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罗岗教授回答:人民大众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是“大众文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是今天的讲座只能做概括性的梳理而无法包揽各种细节性问题。简单来说,人民大众与知识分子间一直保持着双向互动的关系。例如,在“延安文艺”实践中,知识分子走入基层,向群众靠拢,他们不仅要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更需要用作品引导和鼓动群众。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改造着群众,群众也在改造着知识分子。
第二位同学提问:在抗战时期,华南地区运用朗诵诗运动、街头诗等文艺形式宣传爱国抗战思想,几乎同一个时期,延安地区也发起了类似的街头运动,您认为延安的街头运动和华南地区的朗诵运动,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上是否具同构性?罗岗教授回答:这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单就你的表述来看,这两种运动都体现了文艺发展中的媒介转向,将原本私人化的文字阅读行为转变成了一个集体化、具有互动性的表演行为。
第三位同学提问:您提到当代文艺呼唤多元媒介,是否听觉媒介也可以被纳入到“大众文艺”的范畴之中,从而挖掘出文艺的更多潜能?罗岗教授回答:这当然可以。听觉媒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听觉本身就是集体性的,听觉性的意象必然需要言说者和倾听者两种身份的共同在场,听觉文艺的传播本身就营造了一种循环和呼应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