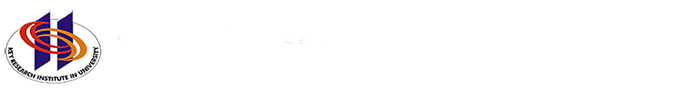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5季第2讲
2025年11月9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五季第二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420教室举行。本期讲座由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沃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教授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笑夷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建青与中山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张米兰担任与谈人。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教授参加了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从社会形式分析路径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特征的讨论,着重于马克思对国家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的批判。博内菲尔德教授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作为独立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并非凌驾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上,而是作为其独立机构从中出现。博内菲尔德教授首先介绍了黑格尔和斯密对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独立力量的必要性的理解,他认为,对于黑格尔和斯密来说,资产阶级社会代表了一个受国家保护的无国家领域。他们明确指出,“自由”经济相当于政府的一种做法,相当于压制阶级斗争、社会去政治化和道德化以及建立和执行基于私有财产法律的游戏规则的一种政治实践。黑格尔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动力使其分化为对抗的阶级关系,因此保持它的资产阶级性质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国家被视作资产阶级社会集中的权力和独立的力量。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获得有价值和广泛的财富必需建立国民政府,以确保秩序和法律,并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来维持私有财产的动态逻辑。因此,斯密没有在一场“几乎不会获得任何优势”的战斗中与资本家对抗,而是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国家通过其公共政策对此负责。
然后,博内菲尔德教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种路径。在他看来,列宁主义将国家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社会民主主义则将国家视作一个根本上独立和中立的领域,其政策反映社会力量间的平衡。而政治形式分析路径批判前两者,拒绝与列宁主义政治理论相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其低估了国家独立于主导社会阶层的独立性;并且拒绝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理论,认为其低估了这种独立性的局限性。博内菲尔德教授主张将国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形式,并且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构成的一种虚假的分离,其本身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上。国家此时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政治形式,正如商品是其经济形式一样,国家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种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其功能是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法律和私有财产。接着,博内菲尔德教授表示,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将所有人视为形式上平等的抽象公民,以掩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国家试图制定并执行游戏规则以确保这种所谓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实质上掩盖了内容的不平等,掩盖了工人为生存被迫出卖劳动力并在劳动过程中隶属于资本家的实质。从而,再生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国家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和财产的有组织力量。对此,博内菲尔德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平等看似赋予工人“自我负责”的自由,实则使其独自承担失业和贫困的风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为持续的阶级斗争,资本家在榨取剩余价值的立场,而工人则争取生存权益。在这种被“平等权利”掩盖的冲突中,最终结果由力量对比决定,而国家正是这种决定性力量的体现,其通过制定工作条件、福利政策等规则进行干预,这些规则常与资本的直接利益相矛盾,揭示了国家在平衡阶级矛盾中的关键角色。
从政治形式分析路径出发,博内菲尔德教授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改善劳动条件的承诺是一种“客观的幻觉”。这种幻觉在于,其试图在资本循环的逻辑内部进行再分配改革,如此看似代表工人利益的政策,实质上未能挑战资本逻辑,其前提恰恰依赖于从工人活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以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反而使得“一种代表劳动利益的社会主义政治”成为经济的延续和确认,使国家成为经济强制的集中形式,最终引导工人阶级去认同统治代表。
在讲座最后,博内菲尔德教授指出,由于资本的全球性,民族国家不能凌驾于资本之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世界市场关系,因此民族国家的概念性是世界市场概念性,在此立场上,博内菲尔德教授强调不应忽视马克思关于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集中力量”概念的丰富内涵。在每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世界市场都是活劳动增殖的决定性力量,那么整个剩余价值生产者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力在世界市场水平上的盈利能力。因此,就民族国家而言,它始终是其国家劳动力在全球竞争力的“规划者”。
在评议与交流环节,马建青教授对博内菲尔德教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其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发展形态,更深刻地认识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今天,人们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国家观,一是阶级国家观,即国家是一定的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工具;二是作为“寄生机体”的国家观,即国家是既寄生于社会又对社会施以尽可能掠夺的可怕机体;三是承担社会职能的国家观,即国家通过行使一定的职能来管理或服务社会。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策略的选择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国家观密切相关:第一种国家观指向暴力革命,第二种国家观指向短暂专政,第三种国家观指向民主改良。他提醒到,只有从这三个方面,才能理解报告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种发展形态的理论逻辑;也只有综合这三个方面,才能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最后,马建青教授与博内菲尔德教授就黑格尔、斯密与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交换了看法。
张米兰老师与博内菲尔德教授围绕对亚当·斯密思想的常见误解展开讨论,强调其理论中常被忽视的复杂性。张米兰博士指出,许多人误以为亚当·斯密完全拥护自发的、由欲望驱动的自由市场,并将其视为解决贫困与贸易等问题的自由机制。然而实际上斯密在著作中极少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且他对其所 设想的“经济人假设”持怀疑态度,尤其关注权力结构与社会教育功能。斯密认为,市场并非纯粹自然或自我调节的体系,而是依赖于国家在两个关键层面发挥作用:一是维护正义与法律秩序,二是承担道德教育职能,以缓解分工对个人精神造成的潜在伤害。因此,国家在平衡市场运作与社会公正之间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随后 ,张米兰老师进一步指出,欲理解斯密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他所处于工业革命早期而面对的是农业尚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其极力支持自由市场走向某种极端的立场是对当时经济现实的回应。因此,对应的历史语境使得斯密的理论具有内在的“两阶段”张力——既倡导市场自由,又强调国家干预的必要性,这种双重性在斯密与赫尔的对比中更为明显。在张米兰老师看来,亚当·斯密在很多方面都与赫尔一致,尤其是在第二阶段——作为国家职能的坚定支持者,但她又指出尤其在教育、道德判断与社会互动等方面,斯密显示出更复杂的立场。尽管斯密在描述市场运行时,常被误解为将之视为自然过程,作者指出这些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构建的,因而具有可干预、可塑造的特性。
而后,来自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的卡沃拉科斯教授与博内菲尔德教授交换了各自不同的见解。他首先质疑为何在该语境下选择使用概念“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而非“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并且认为“社会关系”该表述可能导向某种国家与社会间的虚假分离。另外,他针对如何理解“形式”概念提出问题,究竟是社会关系的凝结还是由社会关系中生成的某种表达,这些社会关系是否同步,意味着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来简单地推翻政府和所有国家。对此,博内菲尔德教授做出回应,说明使用“社会关系”这一概念的来源,并且指出社会关系呈现为事物间关系的形式。针对关于“形式”的提问,博内菲尔德教授指出,社会个体在社会中被自己的产品所掩盖——包括自己创造的系统、政府偏见等。不存在脱离内容的形式,而内容和形式既不相同又相同,因为形式只能是历史特定社会关系的形式,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形式。如果将内容与形式分离,最终只会导向完全的形式主义或存在主义。博内菲尔德教授进一步建议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一句话,“社会关系呈现为事物间关系的形式”,这句话指出我们拥有的是事物间关系,但它们只是以某种否认其存在的形式存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是解密这些形式,将社会构成和社会实践带到形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