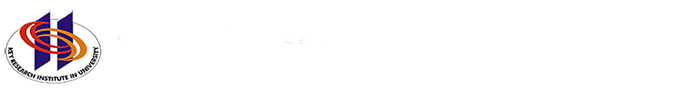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第2期第3讲
2025年6月14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二期第三讲顺利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越,主题为“作为话语的’阵地战’——打开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一种方式”。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担任评议人,马哲所暨哲学系助理教授张米兰担任主持人。
张米兰首先介绍了与会嘉宾,随后陈越以《狱中札记》版本和相关文献的介绍开始了讲座。陈越指出,作为隐喻性话语的“阵地战”一方面相对于真正的科学概念而言还有缺陷,另一方面借助一种隐喻关系所包含的想象力,尤其是一种空间形式,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提供了“概念出现的场所”。他希望通过对“阵地战”话语的讨论和分析,重新展开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一、阵地战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溯源
陈越指出,尽管“阵地战”概念出自葛兰西,但它植根于悠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话语传统,即用战争比喻政治的理论传统。这一传统实质上逆转了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经典命题,转而强调“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其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联结,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新颖性——建立在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权相对分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领导权,以及领导权斗争所要求的全新方式,第一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统帅性主题。这一话语的核心理论功能,是在历史的不平衡发展的体系中,拒绝“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把市民社会开辟为“阵地战”的战场,即把“阵地战”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而非相反;其中包含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批判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脱离并向“游击战”蜕变的倾向。
二、一种新的话语:阵地战作为反军事主义的政治话语
陈越接下来依托《狱中札记》的文本分析,探讨了作为反军事主义框架内的政治话语的“阵地战”的生成逻辑,并揭示了其中蕴含的理论张力。他认为,有效区分战争与政治是运用军事隐喻同时抵制军事主义的关键前提。根据葛兰西的表述,他主张“政治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另一种手段”指的是什么呢?
循此问题,陈越聚焦于“阵地战”话语的理论革新。他指出,“另一种手段”并非根植于战争和政治之间抽象的概念差异,而是依据“1848-1871-1917”这一系列年份的历史断裂及其重构的政治空间距离。当葛兰西将“国家/市民社会”的区分融入其政治思考的二元框架内,“市民社会”和“领导权”概念便得以联结,由此催生了“阵地战”的论述。这一话语统摄的核心创新在于: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制政体的权力关系的新颖性在于“第一次发展成为一个统帅性的主题”,市民社会作为资产阶级权力结构内意识形态机器的载体获得了新的定位;后者意味着需要一种不同于“运动战”的新斗争策略。以“在对手的地盘上战斗”为根本特征的“阵地战”话语,与以往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典型的“运动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运动战”以打碎旧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为目标“阵地战”则旨在夺取阵地,将其转化并确立为自身的“立场”,而非简单地将其摧毁。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借助隐喻探讨政治,锻造了一种具备反军事主义实质的政治话语,并始终强调领导权斗争与普通政治/军事斗争的深刻分野。
三、方法启示:“不要模仿统治阶级的斗争方法”
陈越指出,“阵地战”话语蕴含的方法论启示核心在于拒绝对统治阶级方法的模仿。这一洞见需置于葛兰西对“国家”与“市民社会”虚幻分野的批判背景下理解。葛兰西揭示此分野的虚幻性在于:现实中的统治权本质上是强制(force)与认同(consent)的结合——国家垄断暴力的同时,与市民社会共享意识形态权力。葛兰西意识到,意识形态权力与存在于镇压性机器中的那部分政治权力(狭义的“政权”)的相对分离构成了比“三权分立”更根本的资产阶级权力关系。陈越进一步指出,这两者构成一种非单一肯定性关系。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实为“批判性权力”,其运作方式在于不断地自我分化与复制,由此构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的意识形态空间。在那里,尽管充斥着无尽的“主义”论争,却没有任何一方真正具备消灭对方的意志或能力——因其斗争形态始终被市民社会固有规则预先框定。这种当代意识形态呈现为一种被统治者参与的“游击战”:其表象是“歌颂一部战争机器,并以此反抗国家机器”,然而其性质不过是“在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进行的“游戏”。
一旦与反对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运动战”相脱离,“阵地战”即面临蜕化为一种基于“个体”层面的“游击战”的风险,进而沦为对统治阶级创造和维系阶级剥削条件之策略的模仿。然而,葛兰西的论述中并未包含此种理论转向。在其理论框架内,决定性的胜利仅能奠基于“阵地战”与“运动战”的辩证统一与同步实现。于此,葛兰西重申其核心方法论立场,其核心在于拒绝模仿统治阶级的斗争策略。
四、“阵地战”话语的“剩余意义”
在讲座结尾,陈越重新审视了葛兰西提出“阵地战”话语所依赖的“东方/西方”对立框架。他指出,这一对立框架存在根本的理论缺陷,因其隐含着将西欧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道路视为唯一固定模式的潜在倾向。只有将这种对立置于共时性且不平衡发展的全球体系中加以考察,才能促使葛兰西为适应“西方”战略而刻意压抑的要素返回至“阵地战”话语内部,使其蕴含的“剩余意义”重获批判潜力。
陈越最后强调,“阵地战”话语的核心理论功能在于把“阵地战”作为市民社会本身的前提,而非相反。只有把市民社会主动开辟为“阵地战”的战场,才能利用其“和平的密码”,揭示并挑战其内在规则,分化与限制其权力运作,并在此过程中将其导向更高级的政治实践。
五、评议和讨论
在评议环节,丁耘首先高度肯定了主讲人的洞见深度与分析的严谨性,随后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评论。首先,隐喻并非仅仅是“前概念”或“描述性”的范畴。相反,诸多概念实际是围绕隐喻而建构的。近代哲学中经典的机器和有机体的隐喻就属此类情况。其次,葛兰西在批评“市民社会/国家”的二律背反时,依赖了一些存在问题的概念区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组概念是对“同意”和“暴力”的区分。暴力并不能仅被归属于国家。相反,19世纪末的德国国家哲学认为,教会垄断了精神性的暴力。阿尔都塞也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通过家庭和学校来塑造同意。这意味着同意并非自然生成,而是被系统性地建构的产物,因而不能完全被排除在暴力概念之外。第三,葛兰西的理论被阿尔都塞进一步推进。“阵地战”的隐喻虽然强调或补充了市民社会层面的斗争,但其军事对抗的意象仍然简化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尤其弱化了生产领域作为最核心的“阵地”的重要性。在真实的社会改造过程中,所谓斗争的核心是渗透于人伦日用的生活实践。相反,机器的比喻一定暗含了生产性本身作为其前提。这一点是阿尔都塞对葛兰西作的重要理论提升。最后,葛兰西主张无产阶级“不模仿统治阶级的领导方法”,但此原则和“将群众文化引向高级文化”之间存在张力。高级文化作为有教养者的文化,本身根植于不平等。而无产阶级文化则诉诸普遍的平等。这一矛盾实则是资产阶级自身历史困境的复现。无产阶级若以“高级文化”为模板,则可能复刻资产阶级的文化依附路径,从而陷入自我合法化困境。
对于上述问题,陈越指出葛兰西曾考察过儿童受教育时身体上经历的规训,但的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后来福柯就此出发做出了创新。针对最后一点,陈越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仍然是以资产阶级作为样板的。资产阶级在推翻统治阶级后成为了占据高级文化的新统治阶级,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推翻统治阶级”之后并不应该建立具备等级色彩的文化;尽管要如何实现这一设想是一个难题。
最后,在场老师、同学还向主讲人提出了“领导权概念的主要含义”“知识分子的角色”等问题,主讲人一一做了回答。第二期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