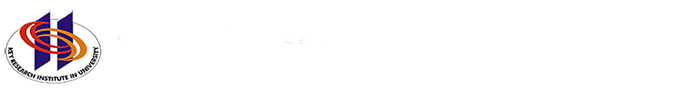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4讲
2025年12月1日上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四讲“天下”,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陈少明教授对干春松教授的学术贡献及影响作了简要介绍,指出干教授在儒家思想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方面的创新性意义。陈少明教授指出,“天下”是中国哲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哲学范畴,对它的讨论也不仅止于哲学界。近十几年乃至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天下”的讨论逐渐兴盛,干春松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一、“天下”的多重内涵
干春松教授首先梳理了“天下”概念的本义。他指出“天下”并非单一维度的范畴,而是包含四个层面:地理空间、等差性统治秩序、完善的治理之道,以及秦汉大一统后收缩入国家话语之中的天下观。
地理空间的“天下” 地理空间的“天下”,通常观念中指“天之所覆”的所有区域,但实际上指所统治的区域,且是实际控制区域与想象控制区域的重叠。干春松教授引用《墨子·非攻下》说明,先秦文献中的“天下”通常出现的是“地理概念”,是空间的概念,且常与“大国”“四海”“天子”等概念并用,既指王朝实际疆域,也包含了想象空间。
在《礼记·王制》的五服制度中,天下被划分为甸服、采服、流服三个层次:天子居中心的甸服,诸侯居采服,边疆民族居流服。这种等差性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中心—边缘”的认知模式。正如邢义田所言:“这个‘四方’既可以是有边界的,即商代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可以是没有边界的,因为理论上商王是天下所有区域的统治者。”干春松教授认为,这种空间想象既包含实际控制区域,也具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统治者往往不强调边界的绝对性,而是以“王者无外”的理念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当然,干春松教授也指出这种统治秩序,遵循一种由中心向四周扩展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形态。
作为最高统治秩序的“天下”作为统治秩序的“天下”,则强调等差性。干春松教授引用《论语·季氏》中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指出不同统治区域的统治原则在根本上不同,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不仅是治理范围的扩大,更是原则的提升。因此,天子之事和诸侯之事完全是两件事: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其治理原则并不相同。
“天下”与“中国”在有的文本中往往同时出现,此时“天下”图景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四面扩散的地理想象。如《战国策·秦策三》里范睢所说:“今韩、魏,中国之处,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齐、赵。”可见,在春秋时期,“中国”是“天下”的中枢和关键。由此,“天下”既可以仅仅指“中国”,也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区域。
作为制度原理的“天下”秩序价值层面的“天下”指向一种“好的统治秩序”,凝结着儒家的治理理念。此时,“天下”秩序强调以道德感染力吸引国民过上好的生活,而非以霸权的方式实现统治。接下来,干春松教授逐一呈现了从《尚书》到《孟子》,再到董仲舒、何休等人对这一最高治理之道的论说。
《尚书·洪范》中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干春松教授指出,这表明“王天下”的内容是公平和爱,孟子则对此阐发更多。在孟子的思想中,王道的出发点是“不忍人之心”,他区分王霸,强调“以德行仁”的感召力优于“以力假仁”的强制力。
汉代,董仲舒和何休对《春秋公羊传》的阐述,说明了“‘大一统’建立之后如何看待统治秩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描绘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渐进式德化之治,何休也认为从所传闻之世到所闻世,治理重心逐渐转移,最终实现德化天下、远近若一。干春松教授强调,公羊学对于大一统的阐述固然是“对于秦汉之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现实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但究其实,乃是儒家王者无外思想的一种逻辑推展”,其本质是“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序扩展,最终实现“万物一体”的太平世界。
4“天下”与大一统国家秦汉以后的天下观,被收缩至大一统国家框架中。干春松教授首先阐明了“得天下”问题,他认为,天下秩序与“治理者”密切相关,统治权的获得往往被解释为“天命”所归,而天命的承担者是“天子”。对此,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认为,先秦天下思想的形成遵循“天—天下—天子”的三部曲,统治权合法性常诉诸天命。
接着,干春松教授详细解释了秦汉时期天下观念的变化。他引用钱穆的观点指出,“先秦诸侯国拥有的‘天下意识’是秦汉大一统国家的价值基础”。秦始皇统一后,不再将“天下”视为抽象概念,而是将其收缩到国家实体中。所以干春松教授认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是“天下”秩序落实的过程,大一统国家形成后出现了“寓天下于国家之中”的现象。汉代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强化现实政权与天意的关系,是“天下寓于国家”的具体方式。
二、东亚视域下的天下观
接下来,干春松教授简要讨论了东亚其他国家对天下观的重构。天下观念在东亚各国呈现出“各表其意”的复杂面貌。其中,日本与朝鲜的天下观尤为典型,呈现出不同于中国的特点。
长期以来,日本以自身更接近儒家道德精神自居,而日本的天下观在江户时代发生转向。干春松教授以山鹿素行为例,指出其思想从朱子学转向“日本主义”,主张日本因“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而优于易姓频繁的中国,自居为儒家道德的新中心。干春松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日本对儒家道德秩序的本土化改造,即将道德中心从中国转向日本。
朝鲜的“中华主义”则采取不同路径。林荧泽提出的“朝鲜中华主义”,认为朝鲜是儒家“中华道”的唯一继承者,但不以天下中心自居。干春松教授引用金观涛的观点:“近代朝鲜在这种天下观指导下,一方面减弱了对清朝朝贡关系的道德认同,另一方面以儒学为符号抗拒清廷、争取自主。”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实际上是通过儒学维护民族自主性,体现了天下观念在不同文明中的适应转化。
三、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带来新的世界图景,由此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传统天下观面临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天下观逐渐被民族国家观念取代。干春松教授梳理了梁启超、列文森等学者的反思,呈现了天下观在近代转型中的思想争锋。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批判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认为缺乏民族意识是中国积弱的根源。干春松教授认为,梁启超的观点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天下观的反思,即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中,天下观的理想性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美国学者列文森则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所以,“‘天下’定义了‘国’,对‘天下’的放弃就是放弃了价值”。列文森的观点揭示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矛盾,即如何在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认同,他的观点也为21世纪重拾天下观埋下了伏笔。
四、近年来“天下”话语的兴起
21世纪以来,“天下”话语重新兴起,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崛起后建立文化自信、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密切相关。干春松教授重点讨论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议。
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极具代表性。干春松教授概括其主张——“天下体系”应以“世界”为最高政治单位,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其核心原则包括:“无外原则”(消除绝对他者)、“关系理性”(强调相互依存)、“孔子改善”(实现共赢),以此替代西方博弈逻辑,追求“无外”的全球秩序。这一理论涵盖地理学(以世界全域为政治空间)、社会学(以民心所向为治理基础)和政治伦理学(追求“世界一家”的理想)这三重维度。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理论试图为全球化时代提供新的秩序方案,即通过传统天下观的资源,构建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秩序。
然而,“天下”话语也面临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葛兆光的批评。葛兆光质疑,某些“天下主义”可能是“世界主义旗号下的民族主义”。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质疑虽提醒我们警惕民族主义,但不应否定天下观的积极意义,天下观所蕴含的“协和万邦”理念,可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启示。
最后,干春松教授总结道,“天下”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话题,无论是从历史角度,从观念角度,还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有很多学者推动了对“天下”的讨论。
五、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陈少明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本次讲座的学术价值。他指出,在通常理解中,“天下”是一个模糊且没有边际的概念,但通过干春松教授的阐述,这一概念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其演变脉络从古代到现代都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陈少明教授认为,干春松教授提到的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天下”的立体轮廓——“天下”如何从一个指代空间和地域的概念,演变为一个价值观念。二是“中国”与“天下”的关系——为何“中国”这一原本在天下体系中指代“中央之国”或“中原”的概念,最终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现代国家称谓的“中国”?陈少明教授以难民问题为例,说明“天下”不仅是传统思想的核心范畴,更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非常具有思想张力的概念。
有同学提问:法家与儒家思想气象存在显著差异,如韩非子强调利益计算,而儒家侧重道德感召。那么,是否可能从地缘政治或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儒家政治哲学?
干春松教授回应:利益考量是政治话题的重要因素,但道义也同样不可或缺,政治秩序没有价值理念的支撑则必然行之不远。比如,当面临冲突时,是选择直接对抗,还是先尝试讲道理、辨明是非,这背后关乎是否有一个公认的道义原则作为更高准则,而完全缺乏道义引领的治理方案是难以持续的。干春松教授也为理解先秦诸子思想提供了建议。读《韩非子》要看到其对话者,法家的许多具体主张背后针对的往往是儒家提出的命题。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他学派辩论的“公共靶子”。因此,读法家著作时,若能意识到其与儒家的这种对话关系,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
哲学系刘伟老师问:“实际控制区域”和“想象控制区域”这两个概念是否具有很强的现代的现实经验,用于描述古代的控制类型是否合理?皇帝制(秦制)实际上消解了天子制(周制),那么周秦、秦汉之间的连续性是否需要反思,如何理解“天下内含于国家”这个命题?
干春松教授回应:“实际控制”一词确实带有现代主权色彩,古代统治更呈中心—边缘的辐射状结构。而使用这组概念意在区分两种空间,一是古人已知且能有效治理的地理范围,二是基于“王者无外”理念而想象出的、理论上应归附的无限空间。
至于历史延续性问题,从周制到秦制,再到汉制,具体制度一直在变化,但在“天下”观念上,历代都共享一个超越于具体政权之上的、关于“天命”和“正统”的秩序理念。后世往往争论某个王朝是属于哪个“德”(如火德、水德),即其在正统序列中的位置,而很少从根本上质疑德运更替、天命转移这一框架本身。这意味着“天下”秩序的合法性是被普遍接受的。这种连续性,使得中国历史呈现出与其他文明不同的路径。尽管具体王朝更迭,但“天下”作为一种秩序理想,构成了一个持续的文化政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