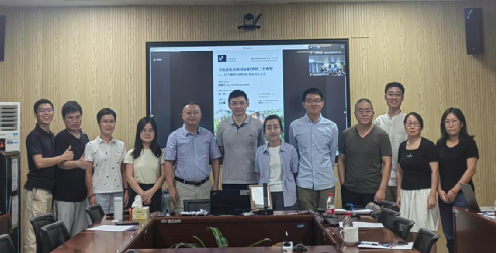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70期
2024年9月25日(星期三)下午,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70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420会议室举办。本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助理教授张米兰主讲,题为“马克思论民族国家转型的三个典型——以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为入手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钊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王兴赛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王兴赛首先向线上线下参加讲座的听众表示欢迎,接着对主讲人、评论人以及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和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作了介绍和回顾。
张米兰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学界批评马克思对民族与民族国家的论断中存在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并且系统地忽视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面对上述批评,较为成功的辩护者凯文·安德森的“复线理论”仍然存在问题,其对马克思理论转变的把握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的纵深分析。
张米兰将马克思关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转型与建构进行了三方面的分类,分为核心国家、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并提出了马克思看待民族问题的三种不同激情:经济激情(财产权)、政治激情(公民权)、民族激情(自决权)。她指出,与晚年著作对资本运动的强调相比,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前后的理论著作中并没有将民族等社会矛盾完全理解为经济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正视了民族联合和民族自决问题的真实社会效应。此外,张米兰还指出,位于三种地位的民族国家在资本运动的一般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有建立边界——打破边界——建立新边界的不同时代任务,这能够解释马克思对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
当前学界研究侧重探讨马克思提出的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构成性要素”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理论意义,而较少关注土地所有制的作用,张米兰提出采取一种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生长出的线索,将民族国家的转型这一上层建筑问题还原到土地所有制在资本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中来。土地所有制的资本化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不同农业发展模式导致了不同水平的革命运动和多样的民族国家形态。张米兰主要通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转型道路中土地所有制及其转型的讨论,深入分析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具体表现,以及这些表现如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相互作用。
张米兰提出,英国和美国的民族国家转型之所以是核心国家类型,不只是因为其发展水平最先进,也是因为其土地所有制转型最符合理想范式。英国土地所有制转型的核心就是“剥削”,表现为“人的自由化”(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土地的自由化”(土地的商品化)。借助分析《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中马克思对比英法德革命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而且是超民族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而普鲁士三月革命则只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英国土地资本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形式转型”是农业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理性化,即以生产力和资本积累的效率为目的;“实质转型”是传统共同体的瓦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法国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对欧洲其他封建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特别是对以波兰为首的仍在农奴制束缚下的东欧农业国家。但法国模式的土地改革最终没有较大经济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贵族不参与农业生产管理,完全放任小农耕作,中央权力分散,无法自上而下地推广土地资本化。针对小块土地所有制小农问题,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土地国有化,这种转变是社会必要性对自然必要性的取代。在此,张米兰提出了英国移民殖民美洲大陆作为对比,并考察了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以及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两国无产阶级政党作出的建议。马克思设想的土地改革路径是介于完全小农私有化与彻底公有化之间的中间路径。张米兰随后总结了德国土地所有制转型问题的特殊性:民族国家建构迟迟未能完成、传统农业社会特征明显、封建贵族地位仍然很高。德国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家产经营到资本主义经营。同时对比马克斯·韦伯对德国土地改革的方案论述了工业经济落后、封建势力顽固的德国面临的独特问题,并对土地国有化进程的困难进行了讨论。
王兴赛指出本次讲座主题的重要性,并将其与中国土地革命与土地改革的历史进行了关联。评论人林钊认为,这是一份选题新颖、视野宽广、资料详实的报告,报告人从土地所有制入手讨论马克思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关切,为读者和听众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信息。而且,它鲜明的史论结合的特点也是值得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习借鉴的优良学风。林钊认为,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是习俗、传统、道德、信仰等因素,将民族问题还原到经济基础层面中间还需要许多过渡的环节。他提出马克思对民族问题的忽视可能是因为他有幸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起,民族国家就总是在战争和对抗中生长和巩固的。再者,如果要从马克思对个别国家的考察中整理出他关于民族国家类型的建构,还需要审察他在当时有限的信息中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是否足够可靠。
王兴赛赞同林钊对民族国家与土地所有制之间关系的疑问,也思考了学界在民族国家研究上从经济基础层面到上层建筑方面的焦点转移。张米兰在回应中提出,土地改革在民族国家转型中可以被划归于“动力”一类中,可以被认为存在亲和性关系,虽然不一定存在强因果性,两者的方式和特征有重要的内在关联。同时,张米兰也强调了特殊的民族性在不同案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波兰与德国划分在同一门类这一问题,张米兰引述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谱系》中的论述为这一分类进行了辩护。就普鲁士个案中的李斯特经济学相关问题,张米兰同意这应当被纳入未来研究。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指出,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曾以治水解释专制,但更深入的历史研究表明专制并不以要治水为前提。与此类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一种重要的史前史。但当代更深入细致的经济史研究似乎表明,圈地运动并没有那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仍从例如《资本论》中的材料、论证及结论出发讨论近代欧洲的土地所有制变迁,在知识和逻辑上似乎是令人不安的。对此,张米兰同意马克思在对前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史料考证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张笑夷教授认为,张米兰通过扎实的文本阅读和分析敏锐地关注到了在民族国家研究中常被忽视却又非常重要的土地所有制这个要素,也许马克思并不是在民族国家问题域内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但试图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要素之一来构建理解欧洲民族国家转型的类型学却是米兰在马克思的启示下获得的洞见。列斐伏尔就曾在马克思的“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的分析中发现被忽视的这一要素,并以此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和以空间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因此,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一要素在理解民族国家转型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生提出,在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相关引用中,报告人对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讨论存在过度阐释嫌疑。张米兰回应道,这里的讨论在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中也有较充分讨论。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其鑫助理教授提出,报告以土地制度为切入面去分析欧洲三个民族国家类型的研究方法论,与韦伯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存在一定差异;大革命及其前后的法国,包括农民在内的第三等级并不以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占有量为主要问题,而主要围绕赋税的等级之间分摊不合理进行政治斗争,这与英国和德国基于土地所有权变动的国家转型—社会变革有所不同。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甲斌助理教授联系巴林顿·摩尔对现代化转型中农业问题的讨论,提出应当注意土地所有制与经营方式的区别,张米兰的报告大量涉及到这两个概念,但对其间的关系似乎缺少充分说明。在回应中,张米兰认为此处的用词的确有待商榷。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张冠博士后认为报告结构中三个国家民族国家构建与民族国家转型之间并不对偶。叙述英国、美国转型的部分,缺少其由民族国家继续转型的有关文本和论述。对此,张米兰表示同意。张米兰也回应了线上参与者的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教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最后发言。他回顾了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十几年来共70期的历程,说明从本期开始因缺乏经费不再给报告人付酬,感谢张米兰老师在无酬条件下对本次研习会的倾情奉献。他还指出研习会新的海报已改为以中山大学南校园的陈寅恪故居和陈寅恪塑像为背景,并借此由头简要阐述了研习会的如下精神追求:一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二是实践哲学研究中心的“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三是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特别希望在以后的研习会上,各位同仁能发扬上述精神,留下各自的批判性纪录。
王兴赛最后对本次讲座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诚挚感谢,向主讲人赠送纪念海报。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