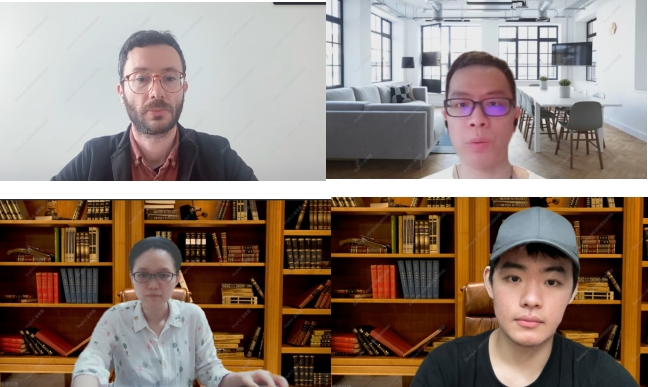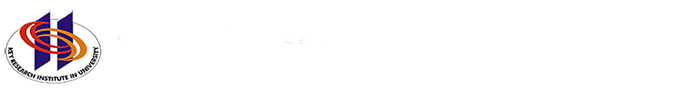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4季第3讲
2024年6月13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四季第三讲在线上成功举办,由巴黎新索邦大学长聘副教授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主讲,题为“从技术唯物主义到技术想象,再回到技术唯物主义”。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深圳科技大学助理教授邓盼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刘畅博士生任学术翻译。
凌菲霞向听众介绍了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巴黎新索邦大学(巴黎第三大学)长聘副教授阿尔贝托·罗梅莱(Alberto Romele)的研究专长为数字诠释学、人工智能的技术想象、大众图像在科技传媒中的运用。凌菲霞特别感谢邓盼推荐罗梅莱参加本系列的活动。
罗梅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经验转向”为原则的技术哲学对于理解当今学界热议的技术主题和方法仍然具有明显的影响力。他着重考察了学者们对海德格尔决定论、悲观主义及其“集置(Gestell)”概念的批判。罗梅莱主张采用诠释学方法来研究技术哲学,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经验态度,而是将其整合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意味着整理出所有技术应用的可能性条件;在较为狭义的层面上,这意味着研究技术应用的符号(文化)可能性条件;在最为狭义的层面上,这意味着要么考虑技术中介的诠释学性质,要么聚焦于特定类型的技术,即那些促进主体与世界之间诠释关系的技术(例如书籍、地图、飞行仪器)。罗梅莱在不否认经验转向原则的前提下,尝试采取不仅思考技术应用,而且考察技术发明和使用过程的符号形式(技术想象)的研究进路。他强调,社会技术想象主要是新兴的、非制度化的,主要来自想传播其愿景的公司或小型利益集团。此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不是任何明确欲望的对象。因此,它们不仅涉及特殊技术,还涉及日常技术。总之,我们必须考虑竞争性想象之间的冲突,承认存在着真正的象征性霸权斗争,因为这对于我们现在或未来的物质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除了进行上述理论探讨,罗梅莱基于具体案例讨论了在媒介与科学传播领域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图像集合具有一种麻醉作用,原因不仅在于缺乏参照标准,还在于缺乏“慎思”。邓盼评论道,罗梅莱的报告中使用了三个重要概念:集置、想象和意识形态。邓盼结合海德格尔的德文、英文文本以及康德的文本,对这些概念做了深入的解读,并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本身并不再是技术,这是否在开启一种存在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技术观?其次,幻想和想象的区别是什么?最后,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罗梅莱回应道,首先,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者们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是有一定洞见的,但是过于简单。事实上,海德格尔的集置概念更加复杂。集置概念和存在的命运相关,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进路。一是将集置看作一种单一的、独特的东西,且为所有的社会文化体系所共有;二是集置的一般性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可以发生更为具体的改变。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进路,那么集置概念既可以是一种危险,也可以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资源。罗梅莱本人希望开显出集置概念的社会文化维度。其次,他认为,幻想和想象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能力,毋宁说,二者是同一种人类想象力的两个极端,都是在将现实的一些碎片要素拼贴起来、重新组合的能力,但是在幻想那里,这种组合的方式是不融贯的、站不住脚的;而在想象那里,这种组合的方式则是融贯的、站得住脚的。最后,罗梅莱指出,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里,意识形态是一种扭曲性的病态意识,但意识形态也有积极的功效,它能够将社会成员的观念、对社会目标的看法统一起来,从而能够将社会团结起来。乌托邦的消极意义在于,它似乎成为了对于现状的一种逃避,它的积极意义则在于,能够成为对现状的一种挑战。凌菲霞的问题是,符号和语言两个概念之间是否有区别?罗梅莱回应道,二者之间既有共同立场,又有具体区别。例如,在人工智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将语言的想象还原为视觉符号的想象,但不能反过来。在当下,他更聚焦于二者之间的共同立场。
最后,罗梅莱衷心感谢主办方与参会人员。凌菲霞感谢了与会师生,并希望大家继续参与支持马哲前沿国际论坛的系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