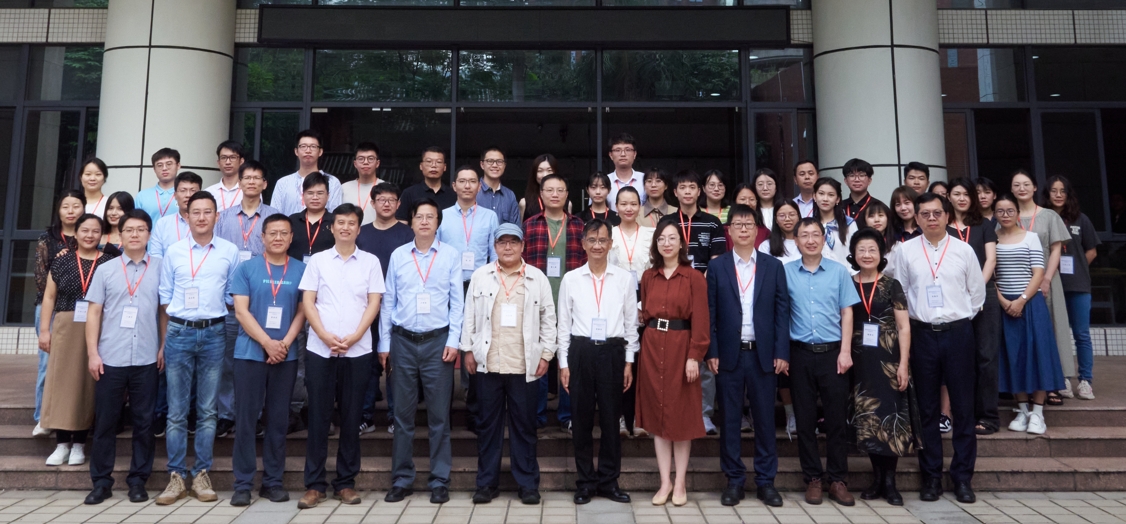“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3年11月3日至11月5日,由中山大学马哲所、哲学系、广东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研究院以及《现代哲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锡昌堂顺利举行。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15个高校、科研单位的老中青学者共计40余人,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农业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探讨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所呈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丰富实践探索。
11月3日上午八点半,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吴重庆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何婉冰副处长作开幕致辞。
何婉冰副处长首先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述诚挚欢迎,随后从时代意义与学科建设两个层面谈了本次会议举办的意义。从时代意义看,集体化时期为中国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立足新时代研究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助于我们理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基本现状,更好地探索符合中国乡村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学科建设上看,跨学科是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着力强调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以问题研究推动学科发展,举办本次会议也是通过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诸多议题为抓手,促进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在这些议题上的学术交流与深入对话。最后,何婉冰副处长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第一单元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主持,四位学者进行会议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徐俊忠教授做了题为《论毛泽东农治思想》的主旨报告。他认为,毛泽东农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合作化而集体化,实现农民组织化;通过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社队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产业形态的多样化,从而创造“在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有利条件。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于西方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胡英泽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也谈农民的“两个阶级性”》。他认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为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以及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积极性就形成两种发展道路的斗争。胡老师由此延展了农村互助合作、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积极性与干部的积极性、集体经济主导性以及个体生产积极性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
台湾海潮智库的林深靖博士的报告题目为《集体与个体的思辨——从台湾农村的互助模式谈起》。他以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高雄东北部美浓镇烟叶生产为例,通过回溯烟叶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集体主义意识,来反思当下工业化市场化社会下个人主义原子化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孟庆延副教授做了以《农村合作化的政治过程与社会基础:以河北西村为中心的讨论》为题的报告。他以华北西村为例,探讨了合作化过程中华北小农经济内在秩序的地方逻辑与“内参制度-典型样板-试点推广”的国家逻辑的互动。
报告结束后,多名学者在评议环节参与讨论。卢晖临教授首先评议,他认为本单元报告都在强调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的一种互助合作模式,哪怕在无集体化运动的台湾也有合作互助模式的生产关系存在,这种生产关系的确需要面对集体和个人积极性的迷思,以及集体制度与原初社会条件的互动。吴重庆教授认为,集体化实践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也是对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大国的中国实现在地工业化、城镇化的现实考量,四位老师的报告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集体化的社会基础与时代需求。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许多人并没有关注集体化实践背后本身关注的真问题,目前进入集体化时期历史的研究的姿态、方位和立场都需要重新思考。熊万胜教授认为,重新思考以何种角色进入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很重要,走向集体化的内在逻辑需要得到关注,还需要思考组织化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使集体化实践的历史经验受益当下。孟庆延副教授认为,当讨论合作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这一阶段变化的时候,我们应当意识到人民公社面对的现实困难并非政治性而是技术性的,诸如消费品的核算、分配等都对公社干部的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徐俊忠教授补充道,当时的中国工业化积累主要不靠农村而靠工业,因为彼时农村农民并无多少剩余,许多通行观点都需要回到当时历史情境条件中再进行检验。
第二单元由徐俊忠教授主持,六位学者做会议报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带头人: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他认为西方学者将中国乡村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理解为“庇护-依从”关系的观点并不准确,集体化时期乡村干部需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群众之间在地位和财富上关系平等,这种平等关系的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体现。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遏制形式主义的经验初探》。集体化中后期之所以能遏制形式主义的蔓延与过度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官僚主义受到大小“民主”的打击、基本生产单位调整到生产队有关。然后,他分析了基层形式主义的基本机制、形成原因和发生过程。最后指出,集体化时期从合理设置基本核算单位、超幅度管理等方面为遏制形式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陈瑜豪的报告题目为《“枫桥经验”六十年:缘起、历程及研究评述》,他介绍了枫桥经验产生的历史条件,并认为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枫桥经验逐渐从基层治理的实践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治理的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本身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核心。
武汉理工大学卜清平副教授报告题目为《“枫桥经验”何以长青》,从政治机会结构、经验禀赋与政府运作三个维度考察“枫桥经验”五十多年发展演变的深层逻辑。枫桥经验的发展,就是从阶级斗争经验向着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经验的转变;也是从自然经验、维稳经验向国家治理经验的转变。
中山大学陈颀副教授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的地权制度分析》。该报告来源于张笑宇博士的论文,通过对农村集体地权的分析,推进对集体的权利理论理解。农村集体化的制度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消解过去的乡绅权威、重塑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集体功能的弱化,则会使得农村治理不得不依附正式官僚体系。如何重构集体权利、重新焕发农村集体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其鑫助理教授报告题目为《“多民族联社”——新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发展的历史先声》。通过对集体化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联社”能让各少数民族发挥各自所长,提高生产水平。“多民族联社”可谓各民族互嵌式现代化的先声。
评议环节由徐俊忠教授简要总结。他认为,本单元讨论启发我们,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需要我们立足常识进入历史场域,从不同角度理解农民为何需要组织起来。
11月4日下午,会议继续进行。第三单元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慧鹏副教授主持,六位学者做会议报告。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奕山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后发工业化与乡村劳动积累》,他从工业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出发分析了后发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并结合新中国初期的独特国情分析了农村集体化时期增加劳动积累在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对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启发性。
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冯裕强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工分稀释化视域下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以广西容县华六大队为例》,他通过对个案村庄的档案分析提出了工分稀释化视角,人民公社以稀释农业生产的工分值的方式在农业之外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为地方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冯裕强认为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率是多元的,具有社会经济性质。
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彦君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机械化对城乡关系的塑造——以山西贾家庄为例》,她以山西贾家庄的农业机械化进程为例,分析了农业技术应用推广与乡村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生产方式是保障技术红利共享的关键,并就农业机械化与城乡关系转向产生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袁剑报告的题目为《集体化时期农业积累的再认识——以四甲大队(1964-1982年)的经济核算为中心》,他分析研究了山东省平度市四甲大队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形成较高的集体提留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中,种植经济作物、开设工厂等获得的收入又对扩大农业积累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岱作了题为《“治水社会”与治水的新中国》的报告,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农田水利建设中群众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魏特夫所谓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的“治水社会”观点不具有适用性。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肖汉臻的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的大队经营管理制度变迁研究——以广东顺德北水大队为例》,他梳理建国初期广东顺德北水大队经营管理制度的变迁,指出集体经济组织如何破除单位间的资源壁垒,实现资源整合。
报告结束后,多名学者参与本单元的评议讨论。张慧鹏副教授认为,第三单元的报告实际都关涉集体时期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虽然集体概念经由苏联传入中国,但集体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则更多体现了基于具体实际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当下的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制于生产要素碎片化,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经济发展也正面临困境,本单元讨论的历史问题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吴重庆教授强调,要关注挖掘集体化时期的村庄文献资料如何能保存下来的背后故事,资料保存完整度不一的村庄可以进行一种类型化的分析,其中可能关涉到意识形态、个人的努力等问题,需要我们进行细致分析。此外,胡英泽教授、孟庆延副教授、龙其鑫助理教授就魏特夫“治水社会”理论与新中国治水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从学术史、历史学等角度展开了补充讨论。
第四单元由熊万胜教授主持,五位学者作会议发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张龙老师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山村农民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以重庆M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逃荒、村庄建立与人口流动的历程为例,指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村内人口流动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在日后的传颂中不断得到强化,在日后集体化时期的合作化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郑玉的报告题目为《自愿互利、互助合作: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托幼服务的探索》,她分析介绍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托幼服务的具体实践及其对当下托幼服务的启示意义。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倩倩的报告题目为《为农村绘蓝图:集体化时期毛泽东规划农村空间的构想》,她认为集体化时期毛泽东规划农村空间格局的构想和我国相关政策改造了中国传统农村小而分散的空间格局,其中的理念为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提供了基础。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龚城的报告题目为《集体化时期的山区农业景观改造与国家整合——基于重庆市巫溪县路乡“定向密植“运动的历史田野考察》,报告受地理条件影响,路乡农业合作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困难反映出一个幅员辽阔、地貌各异的农业大国整合基层力量、发动群众迈向现代化的不易。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秋辰作题为《西南村寨传统地方社会结构下集体化生产的多重表现——以元阳县为例》的报告。她介绍了元阳县村寨在传统社会结构和集体化组织有机结合下的生产实践经验,指出集体化时期生产实际对当地社会的影响,认为集体化在当地既是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又是对传统社会文化的延续。
报告结束后,进行评议环节。熊万胜教授认为,本单元研究有两个主题,一是把集体当做社区来理解,二是集体化时期国家如何进入到特别难进入的地方社区。两个主题的共同特点是引导我们去思考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研究集体化时期,以及如何选择新的层面来重新面对集体化的材料和故事。卢晖临教授认为本单元展现了中山大学年轻学者参与集体化时期研究的潜力,建议大家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找到合适的学术问题,在田野调查和在档案材料基础之上推进研究。常利兵教授提醒同学们在研究时要注意区分1949年至1957年的合作化时期和1958年之后的公社化时期。要进入集体化的历史,不能仅仅依靠上层的政策文件,还要重视基层田野经验。孟庆延副教授认为集体化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延续性与过程中的技术性。一方面,集体化历史中不同时间节点意味着新阶段出现,但每阶段前后都有延续性,要将集体化与革命根据地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要理解农业在集体化中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特别是技术问题。
11月5日上午,会议来到第五单元,由胡英泽教授主持会议,四位学者进行会议报告。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教授报告题目为《革命年代的女屠工:杀猪能手杨美玲的个体生命史》,通过“杀猪少女”杨美玲如何在学毛著的运动氛围中,逐渐成为一名女屠工、全县名片再到普通干部的故事为个案,揭示社会整体背后的人事与制度、结构与条件,梳理集体化时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易莲媛老师做了题为《天气作为媒介:集体化时期的农谚搜集、农村气象学调查与人工降雨》的报告,展现了集体化时期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将农谚、农用气象预测逐渐科学化的历史实践,通过引入新技术,建立天气哨站,再编写、利用农谚完成农用气象预测工作,实现了现代科学预测技术与传统中国所积累的农谚预测经验的高效结合。
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马维强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历史的建构:<翻身>的学术反思》,指出《翻身》和《深翻》两个文本的书写由于作者韩丁个人调研经历的特殊性,其中描写与真实历史情况是存在偏差的。韩丁对土改整党中的消极面相关注不足。我们应当追寻历史的真相,对《翻身》进行学术反思。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黄海平副教授做了题为《“完整的人”再生产:集体劳动对生于20世纪40-50年代农村妇女的社会塑造》的报告,通过其母亲与母亲朋友亲历集体化的生命史个案,指出集体化时期通过让妇女参与集体劳动、公共生活等方式做出了妇女迈向社会主义“完整的人”的实践探索。
报告结束后,进行评议环节。胡英泽教授强调,在集体化时代研究中,研究者应进入历史情境,着重关注地方与国家、个人与国家间的联系,不要把集体化时代想象成“愚公移山”,还应看到其背后的技术支撑。他认为本次论坛中的许多案例研究很好体现了“两个结合”。徐俊忠教授结合自身集体生活经历,强调对气象技术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地走进历史场域中。不仅是农业需要天气预报,渔业更是离不开天气预报,气象网、水文网等气象预测设施是农业生产乃至农业渔业从业人员生命的保障。熊万胜教授认为,集体化时期的生活史应当有不同于社会史研究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史反映社会史,而研究个体的生活史要更注重生活内在的意义。
会议的第六单元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谭群玉教授主持,七位学者作会议发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张和清教授与硕士研究生戴容成报告的题目是《集体福利保护弱者:广东中山市崖口村的实践与启示》,首先,他们介绍了崖口村的概况以及村内“菩萨养老”、敬老基金会等保护弱者的实践举措。崖口村的实践证明,推动社区集体主导型发展能够增强社区自治发展能力,对中国农村走互助合作道路具有借鉴意义。
中共宁夏区委党校马思雯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能人”带动乡村集体经济的原因探析——基于宁夏庆华村和深沟村的案例研究》。她以宁夏区庆华村和深沟村的集体经济为案例,分析了村庄“能人”带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即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和获取政策性帮扶能力。
广州理工学院黎锦贤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小农困境——基于珠海白蕉镇海鲈鱼家庭养殖户的研究》,以珠海市白蕉镇海鲈鱼养殖业为案例进行分析,当前小农户生产模式在市场中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都遭到挤压,需要在产业现代化中另寻出路。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思敏助理教授作了题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农业发展之路——围绕<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展开》的报告。从实践和制度设计、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处理三大关系四个方面探讨了毛泽东对农业发展之路的探索。
国家烟草专卖局战伟龙作了题为《政治与教化:集体化时期中共培育新农民研究——围绕<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展开》的报告。从“为什么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民?”两个问题中切入,总结了中共培育新农民的路径,他认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需从共产党乡村树人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激发农民的主体性。
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素梅报告的题目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的农业集体化思想》,她从农业的重要性、农业所有制变革及推进方式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三个角度展开,阐释了毛泽东农业建设思想的意义。
报告结束后,评议环节有多位学者发言。熊万胜教授指出,在集体经济发展中能人“带动”与能人“带领”是有所区别的。卢晖临教授则认为,分析乡村中的“能人带动”除了聚焦“能”的角度来谈,还应该聚焦如何“带”,即能人如何在乡村做成组织工作的丰富实践。林深靖博士感慨,在西方“公社”只止于理论上的“乌托邦”、“空想”,而对中国而言则有着基于实际国情而开展的丰富的实践探索。胡英泽教授认为集体化研究需要有“材料-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的自觉。常利兵教授认为,研究《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要更多把论述与社会历史材料相结合。
11月5日中午,随着第六单元结束,持续一天半的学术研讨进入尾声。会议闭幕式由谭群玉教授主持,徐俊忠教授、吴重庆教授做总结发言。
徐俊忠教授感谢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盛赞他们的点评使与会的年轻老师和学生受益无穷。徐俊忠教授强调,第一,中国农村的路该怎么走,这条路绝不在专家的脑袋里,而是在实践和历史当中,集体经济时期不能被遗忘,它不仅是一个学术的宝库,更对现实有重大启发意义;第二,研究中国社会需要有方法论上的自觉,应当从历史分析开始,而非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三,要走出书斋,眼光向下,深入生活和历史的场域,激活我们的肉体感觉和精神感觉,去发现研究的资料和意义;第四,不要低估前人的智慧,尤其不要低估被置于绝地而经由血与火走过来的革命党人的智慧。
吴重庆教授对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提出三点展望:首先,集体化之“化”应值得我们更深入去分析和阐释,它既是实践的“变化”,也是教化之“化”,集体化在家庭与国家之间增加了“集体”一级,引发了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等诸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其次,我们一定要看到集体化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研究集体化不是要唱赞歌,而是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利益分配、组织管理、社会观念等方面的困境,看到每一个中国农民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中是如何调整、自处和适应的。再次,应当注意国家的出场和人的在场,应当超越惯常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在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中理解集体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人的复杂性,看到人的生活过程,让材料“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