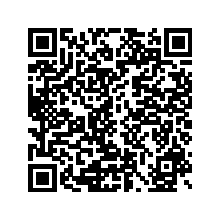实践哲学读书会第11期
2018年4月26日下午,“实践哲学读书会”第11期在锡昌堂515室举行。本次读书会邀请朱刚教授对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进行导读,主题为:形而上学作为伦理学——读《总体与无限》。
朱刚教授首先将该书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框架进行了简要梳理和勾勒,以带动大家一起思考。他认为,列维纳斯之所以为人所知,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伦理学家”,其主要的特色就在于强调自我对他者的一种伦理关系,并视之为哲学的主要问题。他的思想主要是在伦理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等等这些领域。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但他并不试图为伦理学提供一个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伦理规则。相反,他抵制这种做法。因为这在他看来恰恰是不伦理的。他的这些思考本来是要回答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应该是研究作为在此岸的、具有形而上学欲望的我同所要追求的作为彼岸的形而上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同形而上学的关联很微妙。在他看来,将自我的权力进行过度扩张,以至跨越了自我和形而上者之间距离,从而将对方融化了,即认识、掌握了它,这同形而上学背道而驰。因为你对彼岸的形而上者施加了暴力,把它对象化、统一化了。而另一种极端倾向,即不伸展我的主体权利,保持自我的极度谦卑,无条件放弃自我主体权利,归顺到彼岸去,放弃自我。这种做法在他看来也不行。因为这种放弃自我的独立与自由的做法,意味着不再有一个主体来尊重、侍奉那个形而上者,以保持二者的差异性,那个形而上者需要主体。所以你还得保持自由、独立,但是不能使用暴力、过分伸展你的权力。这种微妙的关系,即他所讲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作为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伦理学。
在这种关系中,自我是具有行为欲望的,而他者就是我所欲望的绝对处在自我权力范围之外的一个绝对他者。只有自我与绝对的他者处于这样一种伦理关系中,而不是处于其他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经济关系等等之中,才能实现列维纳斯所说的那种行为关系。因此,他认为,形而上学只能作为历史才能实现。
列维纳斯一开始就谈了形而上学,而且他把形而上学实现并落实到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他这种理解,对于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很好的启示意义。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事实上都只是不同类型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会碰见很多问题,而列维纳斯针对的正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痛的人间悲剧之经验教训的思考。这当然同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时期的德国,犹太人被排斥到极致的历史有关。列维纳斯作为犹太人,他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俄国革命、二战,期间不断飘落各地,受到很大的心灵冲击。他的家人中有很多人被屠杀。他对那种铭刻在种族上的概念,被驱逐的体验,深入到他的思想精神层面。他的思考非常彻底,也非常激进。这对于我们从哲学上和实践上来思考这类的问题会很有启发。